《在劫難逃》這樣玩穿越才高級?
獨生女意外去世,家庭破裂。心煩意亂的刑警隊長張海峰開始得過且過,躲在人山人海中,獨自舔舐傷口,卻無法逃脫自暴自棄的心理陷阱。沒想到,報復(fù)者趙彬彬正在逼近,因為張海峰的前妻喬欣被趙彬彬綁架了,在老同事的幫助下,張海峰又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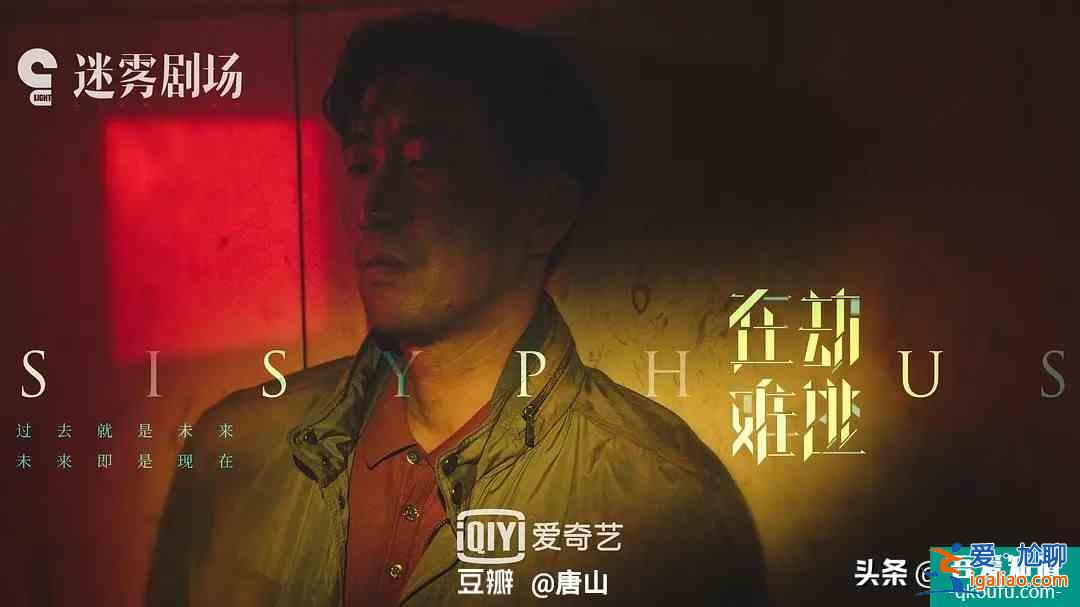
這是愛奇藝懸疑劇場第四部,—— 《在劫難逃》。這部劇的“核心”在于:
第一,趙彬彬這么年輕,他和張海峰之間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為什么這么固執(zhí)?
第二,為了逃避女兒去世的事實,選擇了自暴自棄的生活,張燦海峰康復(fù)了嗎?
第三,張海峰的女兒當(dāng)年是怎么死的?真的只是意外嗎?
這三個“隱藏按鈕”看似不太難懂,但卻足夠好奇:這么少量的故事能支撐12集嗎?劇情會不會變得冗長緩慢?顯然,這些問題是傳統(tǒng)的“設(shè)定-展開”懸疑手段無法回答的。
令人震驚的是,看完《在劫難逃》的前三集,我發(fā)現(xiàn)這部劇的節(jié)奏異常清爽工整,就像一部美劇,一氣呵成12集。此外,有王千源、齊等演員的精彩表演,稱贊其“優(yōu)秀”也不為過。

還要交叉,看你用在哪里。
在當(dāng)下的影視劇中,不同時空之間的“穿越”已經(jīng)成為一種常見的橋梁。而“穿越”真的只是一種低級的影視手法嗎?真的只是開玩笑嗎?不同的觀眾對“穿越”有不同的看法。
齊飾演的趙敏其實還不錯。畢竟角色的空間太大,不容易發(fā)<愛尬聊_百科詞條>揮到這種程度。
其實在文學(xué)領(lǐng)域,穿越已經(jīng)存在了幾千年。艾倫羅伯-格里爾率先將穿越技術(shù)引入影視作品,樹立了一個榜樣。在《去年在馬里安巴》 《歐洲快車》等影片中,交叉作為一種結(jié)構(gòu)性因素而存在。也就是說,在細節(jié)上,我們忠于正常的時間線,但在因果設(shè)定上,我們顛倒時間順序,啟發(fā)讀者思考:我們現(xiàn)有的對世界的理解是否正確?我們理解的因果關(guān)系真的存在嗎?
艾倫羅布格里爾是“新小說派”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世界著名的導(dǎo)演。他的作品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jié)金獅獎。艾倫羅布-格里爾喜歡穿越,因為他在挑戰(zhàn)“必須如此”、“這就是真理”等世俗觀念。我們把這種手法稱為結(jié)構(gòu)性的穿越手法,因為在他的影視作品中,穿越是一種結(jié)構(gòu)性的因素,而不是敘事性的元素。
對于《在劫難逃》這樣的原創(chuàng)故事,它的創(chuàng)意在于將這種手法引入到類型片和電視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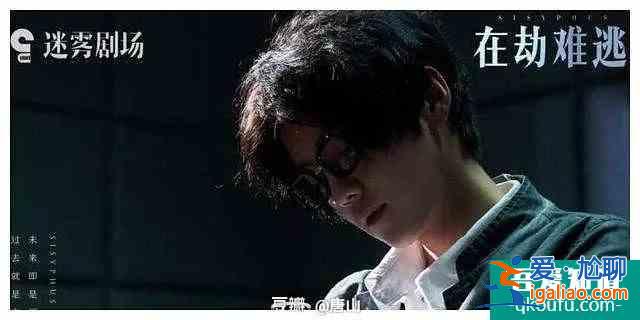
單看《在劫難逃》的一集,幾乎看不到穿越的內(nèi)容,但每次張海峰歷盡艱辛成功破案,當(dāng)趙彬彬投降時,最后都會出現(xiàn)意外。伴隨著這場災(zāi)難,所有的努力都被用來清理——張海峰,仿佛它正在經(jīng)歷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的痛苦懲罰,一次又一次地將巨石推到山頂,看著它一次又一次地滑落。生活糾纏在無用的工作中,永遠得不到解脫。(有趣的是,《在劫難逃》的英文名是《西西弗斯》)
于是,張海峰和趙彬彬穿越回故事的原點,重新開始游戲。每一個新的游戲,都會產(chǎn)生新的信息,引導(dǎo)觀眾一步一步接近真相,直到案件徹底解決。
用好它有三個好處。
《在劫難逃》中,穿越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顯著因素,而是一個基本框架。這樣,至少有三個明顯的好處:
首先是全新的連載模式:懸疑系列的困境在于“隱藏按鈕”永遠是一次性的,新的“隱藏按鈕”要在出現(xiàn)新案件時重新設(shè)置,但每一個新的“隱藏按鈕”都在挑戰(zhàn)觀眾被調(diào)侃和更高的需求。結(jié)果就是男主角要像機器人一樣一個個破案,觀眾的興趣卻越來越低。然而《在劫難逃》卻通過穿越,將“一個又一個新案件”變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舊案件”,從而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敘事殿堂。
其次,很容易理解:這種不斷重頭再來,不斷重新開始,最后過關(guān)的敘事方式,與電子游戲的邏輯高度一致。對于數(shù)字時代的原住民來說,這種敘事模式太善良了。因為日常的接觸,已經(jīng)成為他們了解自己生活的基本邏輯,完全不需要解釋。
三是彌補了懸疑劇封閉敘事結(jié)構(gòu)的短板:在重視“寓教于樂”、“以文載道”的文化氛圍中,國產(chǎn)懸疑劇的結(jié)局往往是固定的,即壞人一定失敗,好人一定成功。中國觀眾對封閉式結(jié)局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們喜歡懸疑,因為它不確定。如果有答案,觀眾為什么還要再看一遍?以往的懸疑劇只能采取過程多變、結(jié)果固定的敘事策略,顯示出其鑿痕。穿越結(jié)構(gòu)正好突破了這個困境。在《在劫難逃》的前三集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次穿越后的結(jié)果都是多變而開放的,這會吸引我們觀眾更加專注于故事發(fā)展。畢竟,任何疏忽都可能導(dǎo)致悲劇。
在這樣一個故事過多的時代,“講什么”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講”。正確的敘事策略會使熟悉的故事陌生化,創(chuàng)造新的審美空間。
103010之所以讓人眼前一亮,是因為它懂得“說話”,能把一種似乎被很多人使用過的穿越技巧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不用說,王千源的表現(xiàn),哪里是基礎(chǔ),想要保持低調(diào),實力是不允許的。
快節(jié)奏是王道。
003010通過結(jié)構(gòu)穿越手法很好地解決了“怎么講”的問題,產(chǎn)生的最直接紅利就是敘事節(jié)奏異常鮮明。
p> 在我們的美學(xué)教育中,對敘事節(jié)奏缺乏足夠重視,但對當(dāng)代觀眾來說,敘事節(jié)奏可能意味著一切——真實感是通過敘事形成的,電視劇中的“事”都是虛構(gòu),“敘”才是重點。對于懸疑劇來說,尤其如此。因為懸疑劇講的是兩個故事:犯罪的故事和破案的故事。故事量天然大于普通故事,想把這兩個故事都講好,必須情節(jié)推著人走,而不能像文藝片那樣,為了塑造“人”,不惜讓情節(jié)慢下來。換言之,只有快,懸疑劇才能給觀眾以真實感,才會讓他們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而非是編造的。
國產(chǎn)懸疑劇往往忽視節(jié)奏,因為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太重意象性,而非具象性。
所謂“意象性”,其實就是用外部環(huán)境來表達內(nèi)心感受。比如:主角出現(xiàn),必然風(fēng)景如畫;情節(jié)轉(zhuǎn)向低潮時,必然電閃雷鳴……雖然很抒情,卻因創(chuàng)作者太居高臨下,自以為擁有燮理陰陽之能,反而使觀眾無法進入股市。
《在劫難逃》好看,在于具象性的力量——鏡頭中出現(xiàn)一把刀,這把刀在情節(jié)中就會發(fā)揮作用,而不只是搞搞氣氛。在《在劫難逃》中,看不到煙波浩渺、仙風(fēng)道骨,只有器物堅硬的表面。
在《在劫難逃》中,敘事呈現(xiàn)出加速趨勢,即情節(jié)變化越來越快,這正是結(jié)構(gòu)性穿越手法帶來的優(yōu)勢——無需再介紹案情背景、人物,特別是每次穿越回來,張海峰的信息都會增加,他能預(yù)知案情的走向,他只需拆解新困境,以及解決根本之問:趙彬彬為何如此糾纏他。
窮盡一個個案的所有可能,比大殺四方、無案不破,在敘事上,實在從容太多,只需看過《在劫難逃》三集,必然會被它的節(jié)奏所打動,大呼過癮。
必須說,鹿晗的表演太出彩了,他以不同的形象出場,每個都到位,成名演員能接受這樣的挑戰(zhàn),甘心做配角,實在讓人敬佩。
這部劇站在了三位巨人肩上
在《在劫難逃》中,結(jié)構(gòu)性穿越手法還產(chǎn)生了另外一個紅利,就是給人物塑造帶來更多空間。

一般來說,懸疑劇最易落入人設(shè)黑白分明的窠臼中,只能塑造“扁平人物”,很難呈現(xiàn)“圓形人物”。“扁平人物”與“圓形人物”是著名作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提出的概念,所謂“扁平人物”,指“某種單一色彩或特質(zhì)”的人物,即漫畫式人物,其優(yōu)點是便于記憶,但更適合戲劇。至于“圓形人物”,則具有多面性、復(fù)雜性,他們有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很難用一個詞來概括。
在很長時期,人們認為類型影視劇只應(yīng)塑造“扁平人物”,所以“扁平人物”又被稱為“類型人物”。懸疑劇尤其如此,因它對敘事節(jié)奏要求太高,人物只是情節(jié)的一個因素,而不能相反。
然而,《在劫難逃》中的張海峰與趙彬彬都帶有“圓形人物”的色彩:
張海峰屢戰(zhàn)屢敗,他不是英雄,他是被趙彬彬拉入案情的,他依然無法擺脫曾經(jīng)的折磨,所以他與老同事間合作不默契,經(jīng)常沉入自己的天地中。
趙彬彬也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壞人,他衣著楚楚,相貌陽光,他并不老謀深算,甚至?xí)粏剃看驎灒瑓s能幾次笑在最后。他所懷的怨恨如此之大,與他的經(jīng)歷、形象很難匹配。
然而,《在劫難逃》也給演員設(shè)置了巨大困難:畢竟不是人人能演好“圓形人物”的。好在,王千源與鹿晗的表現(xiàn)堪稱精彩,尤其是鹿晗,一改習(xí)慣的表演風(fēng)格。在《在劫難逃》中,觀眾將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鹿晗,一個讓人敬重的、會演戲的鹿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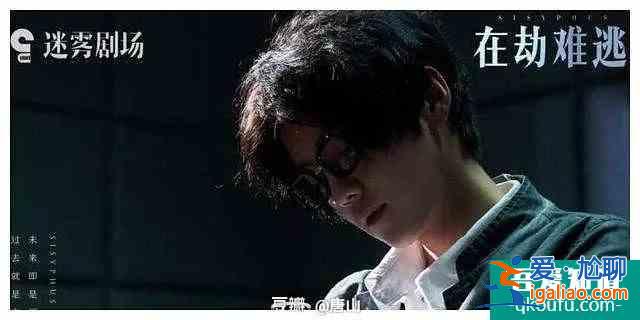
穿越人人會,但如何把穿越玩好,《在劫難逃》這個原創(chuàng)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創(chuàng)造了一個典范。這個典范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站在加繆、阿蘭·羅伯—葛里耶、福斯特的肩膀上,厚積薄發(fā)而成。從一部懸疑劇中,品味出人文精神,這可能正是《在劫難逃》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