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歲的媽媽 “28歲”的節育環?
澎湃新聞消息,正月十二,小琪的生日,她陪母親去取環。
V形、形狀記憶合金材料,又被稱為母愛款,這超出小琪母親的想象,一直以來,她并不知道體內這枚與自己相處16年的節育環長什么樣。
尾戒大小、圓環形狀、銅質,Polly盯著眼前從母親體內取出的節育環。這一年,Polly的母親54歲,節育環在她身體里住了28年。
Polly覺得,它仿佛是母親生育的整個閉環,結束了。媽媽徹底告別她女性生涯里,包括我在內的生育部分了。
絕經后,取節育環被提到了靜湖的日程上,這是她人生中第二枚也是最后一枚節育環。她趕在2024年的農歷新年前,把一切收拾利索了從此,她要一身輕松地邁入人生后半程。
節育環,又叫宮內節育器,把它放在子宮里,可以通過刮擦子宮壁造成無菌性炎癥,影響受精卵正常著床受孕,這種避孕方式在中國被廣泛使用。根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2017年,中國3.53億育齡婦女中,節育環的使用比例為52.18%。
如今,節育環已不再被年輕一代女性廣為使用,但相關的討論越來越多。以此為切入點,關于生育、女性身體、女性選擇、男女關系、家庭關系、性、生命等話題全面鋪開。節育環,這個埋藏在不少女性體內的小小物件,勾起了女性與自身身體、不同代女性之間,跨越漫長時光的一場場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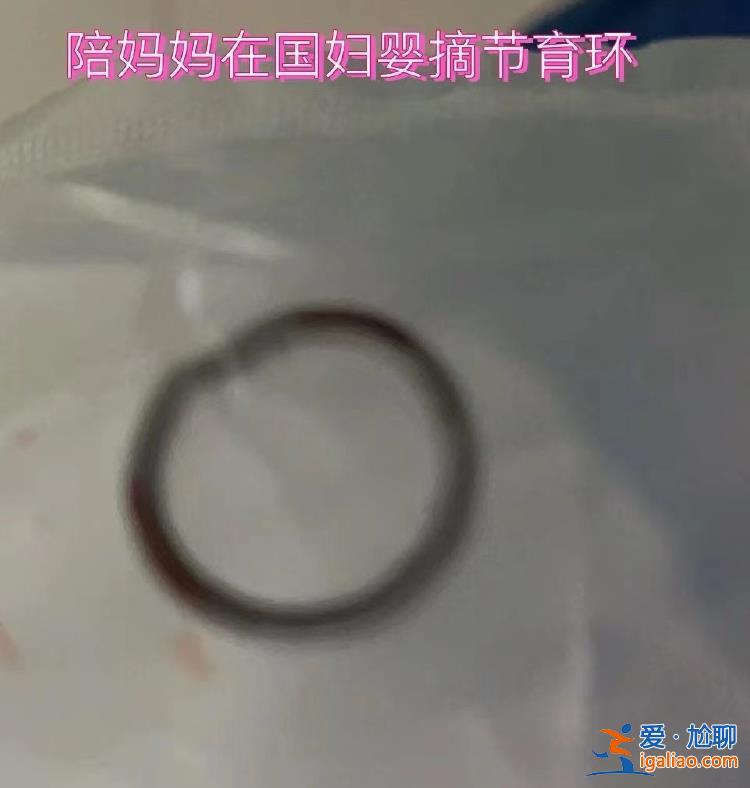
與環共處
Polly記得小時候,曾從父母的溝通中隱隱聽說過節育環,但對此全無概念。
此后成長的十數年,節育環這個詞沒再出現過,直到近些年在社交網絡刷到關于此的科普,向母親一打聽,她才知道母親帶環已超過20年。
Polly的母親生于1968年,和當時的政策有關,那個時候大家可選的避孕方式可能基本只有這一種,所以媽媽也會理所當然地覺得要去上節育環。Polly說。
70后的靜湖是在流產后決定去上環的。
1997年女兒出生后,靜湖的子宮內先后埋過兩枚節育環,一枚在2005年,經歷一次流產后;一枚在2018年,她意識到子宮內的節育環到期退役,又去替換了一枚。
春節還沒正式過完,正月十二,小琪陪著母親走進醫院。
這天是小琪的生日。25年前,母親的肚子在生產時被剖開一刀;25年后,一個放了近16年的節育環被從母親的子宮取出。算上從2000年開始戴了8年的T形環,小琪母親已經和節育環共處24年。

取環之路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計劃生育科主任醫師何曉英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當前,中國女性最常使用的是O形金屬節育器,建議使用時間為15-20年,是保質期相對長的一款;還有包括帶銅T形、活性伽馬形等不同的活性節育器,此外還有吉妮節育器、吉娜節育器、曼月樂等,它們的建議使用年限在5-10年不等。
顯然,Polly媽媽的這只環已超出年限很久,她開始擔心這枚小環會對母親的身體造成傷害。但為了便于取環,只能再等等更合適的時機。待到母親絕經后,2021年底到2022年初,母親和一個相熟的朋友一道,先去所在區的中心醫院門診摘環。但因為節育環的位置不佳等原因,母親的首次取環并未成功。
經歷疫情的間隔,待到2022年下半年,Polly媽媽才成功進行了二次取環,那時她已經54歲,節育環已在體內28年左右。
Polly在社交平臺認真記錄下了這個流程:掛了一家三甲婦產科專科醫院計劃生育科的號,做了B超、驗血、心電圖、CT、盆腔平片等各種檢驗,前后經歷一周,終于在一場全麻手術后,母親子宮內那枚小小的環被拿了出來。時至今日,這條帖子的下面還有不少女孩在咨詢著如何帶媽媽取環。
Polly告訴記者,手術后母親經歷了大概一周的恢復期。那一周內,母親的下體會無征兆地流血,腰也酸得厲害。操著衛生巾熬過一周,這枚節育環留給母親身體的痕跡漸漸消散。

小琪的母親之所以取環,是因異常的子宮出血。出血點經檢查,是一顆接近5厘米的子宮肌瘤,具體原因無法判斷,不排除節育環引發出血的可能。主治醫生建議做宮腔鏡手術,取環的同時刮取子宮內膜做病理檢查。
正月十二,這枚當時還算是新上市的高級款節育環從母親體內取出,它的保質期最多15年。醫生告訴小琪,這枚節育環在媽媽體內已經移位,和正常狀態相比旋轉了90度,但媽媽歷年的體檢報告里卻顯示宮內節育器位置正常。
母親看到這枚V形節育環的反應卻是吃驚:怎么是這個形狀的?這么多年來,小琪母親一直以為自己上的是O形或T形環。
告別節育環
小小的,像尾戒,血跡還留有一點,銅質的,沒有生銹。Polly記得自己看到這枚小節育環的感慨:就是這么個小小的東西,能夠在媽媽體內起到避孕的作用,很神奇。
她掂了掂這枚分量既輕又重的圓環:它像是我母親完成生育的一整個閉環。生育不易,避孕亦不易,希望媽媽之后可以更快樂地做她自己。
50歲,閉經7個月,逐漸出現更年期癥狀,心態也很微妙,有種貓一天狗一天的感覺,從今天起,定位中年少女。2024年1月21日,靜湖在社交平臺發了這段話,宣告自己進入了人生新階段兩天前的1月19日,她終于通過手術取下了自己體內的節育環。
靜湖是那種想對自己身體和情緒有掌控力的女性,因而天命之年回頭望,她自覺算得上事業有成、家庭美滿。這種掌控力也體現在節育環一事上2023年5月絕經,2024年1月便去醫院了斷此事絕經后半年,2024年農歷新年前,靜湖覺得是告別節育環最好的時間段。
一共跑了5次醫院,繁瑣肯定是的,但我會覺得,這也是我檢驗自己更年期后情緒管理的一部分。靜湖笑說,我要檢驗自己能不能把這些步驟都心平氣和地理清楚。
而在做完手術清醒后,靜湖腦子里轉過了幾個念頭,一方面,我其實是感謝這個節育環的,它為我保駕護航了很多年。另一方面,我在絕經后取出這枚節育環,會覺得心理和生理上到那時才真正地實現了同頻。
取環手術由此成為靜湖人生旅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這宣告著,我人生中要拼搏、爬坡的階段已經過去。接下來,可以比較坦然、松弛地邁入人生后半程。

專家:過了保質期或絕經后,別忘取出節育環
我們呼吁,在使用年限到了以后,應盡快取出節育環,以避免節育器走形、取出困難,或對子宮造成別的傷害。此外,由于女性絕經后子節育環嵌頓,異位的概率和取環的危險系數都會上升,因此在絕經后的半年至一年,女性也應盡快完成取環。作為計劃生育科的醫生,何曉英介紹,女性如在還未絕經時取環,可選擇在經期干凈后3~7天時,前去取環,不要害怕,那個時間節育環一拉就出來,取出并不麻煩,也不會很痛苦。
關于節育環的話題,在網上爭議不斷。曾有人解讀說,節育環是靠讓女性子宮不斷發炎從而達到避孕效果。對此,何曉英給予解釋。
目前網上有人對節育環的理解,可能是有一點誤區。她從宮內節育器的運作機制說起,主要有三:一是機械作用,像遠古時有人給駱駝放個石頭占據宮腔,以起到避孕作用;二是理化特征,例如有的節育器里含銅,這部分銅離子可造成無菌性的炎癥,促使精子死亡,即在銅離子的環境當中,受精卵不容易著床;第三是生物學作用,節育器會在宮腔局部形成一個免疫微環境,分泌一些IgG和IgM,胚泡會在這樣的免疫微環境里崩潰,無法著床。
我們好像看到炎癥,就覺得是一種傷害,不是這樣的。何曉英表示,這是一種無菌性的炎癥,要達到的是炎性反應,這種反應是炎癥的微表達,不對身體造成創傷。事實上,人體的很多部分會有這樣的炎癥的微表達,這是具有保護性的表達。
在科室,何曉英觀察到比較常見的來取環的女性,大多在上世紀70年代前出生,其中年紀最大的有85歲,一些人會忘了自己戴過節育環,或者不重視。等到下體出血,或者要做核磁共振了,才想到來取。
她坦言,現在來主動要求放節育環的女性確在減少,比較常見的放環情況出現在女性完成人流手術后、不想再承受避孕失敗帶來的痛苦。另一種,則是用節育環一并治療其他的婦科疾病,比如有女性經血過多,可能會放置一種叫曼月樂的節育器在體內,依托其定時釋放的孕激素,在避孕的同時達到治療效果。

不同代的中國女性和避孕
在何曉英的觀察中,不同代的中國女性,避孕措施有著較為明顯的劃分:50后的婦女以結扎為主;60后以帶節育環為主;70后很多到了中年,有婦科疾病后可能會想到上節育環;80-90后則較為推崇口服避孕藥。
而從避孕的層面,何曉英介紹,避孕套在國內仍是最為常見的避孕措施,但它不能算作高效避孕措施。僅從女性高效避孕的角度出發,措施包括避孕針、避孕藥、皮下埋植和節育環等。
這幾種方式應用各有不同的點,避孕針需要定期來注射,避孕藥要堅持每天服用,皮下埋植和節育器需要來醫院讓醫生放置。何曉英補充介紹,目前來說還沒有完美的避孕方式,可能有的會影響月經,有的會增加體重,有的會導致腰酸等不適。各人還是應該根據各人的情況進行選擇。
目前或許要女性去承擔避孕的情況還是更多一點,但其實我們也會希望,給兩性都能研究出相對完備、無害、便捷的避孕措施,社會對于避孕主體的考量,或許也應該更平衡。采訪的最后,Polly向記者感慨,女性在生育包括養育上,已經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作出很大的犧牲,而避孕的主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交給女性的,這種理所當然并不公平,可以說在身心上都給女性帶來了更多一層的傷害。
避孕主體在男性還是女性,確實涉及一個家庭里誰愿意做出犧牲的問題,每個家庭情況是不同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也向記者表達了看法,在我看來,不應該一味地唾棄節育環或者其他女性避孕措施。為什么不能把它們看作是女性將避孕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一種方式?把避孕的可能性交給對方,如果對方靠不住,我想給女性帶來的傷害只會更大。
編輯:楊雁琳責編:吳忠蘭審核:馮飛
